钟扬老师,我们的问题,永远不可能有回答了
相关阅读:钟扬援助基金设立
著名植物学家、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钟扬,9月25日在内蒙古遭遇车祸,不幸离世,年仅53岁。
我们的问题永远不可能有回答了
有人说钟扬高调,他的媒体曝光率确实高,但实际上,他只是十分乐意做科普。钟扬热衷于青少年科普活动,包括为中小学生举行科普讲座、撰写和翻译科普著作。他还承担上海科技馆和自然博物馆的中英文图文版工作。DNA结构发现者詹姆斯·沃森的传记《基因女郎伽莫夫——发现双螺旋之后》和访谈录《DNA博士》等书就是由他的团队翻译成中文。
钟扬在一次访谈中说,他相信科学能深入儿童的心灵。他在给杂志《科学队长》中解释他为什么爱给孩子做科普——“一个小孩子其实很难靠几本书来准确了解科学道理。不过,书中那些遥远的故事及其承载的有趣知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渗透进脑海。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或场合,这些似是而非的知识也许会与新的思想活动碰撞出火花,并以独特的科学气质展现出来。只有此时,长大的孩子才能真正体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人生意境。”
而他自己的好奇心也有父母引导。他回忆小学二年级时从书中读到了一点电池的知识,立即就将家里手电筒中的大电池倒出来,用铁钉打出小洞,再往洞内灌各种各样能找到的酸性液体。他的母亲是中学化学老师,看到那一堆废电池时,没有责怪他,还将他带到化学实验室去观摩实验课。
他的双胞胎儿子,均以植物命名:云杉和云实。一个是裸子植物,一个是被子植物。他认为,只要有可能都应当用植物给孩子命名,“如果植物取名蔚然成风,会给分类学在社会上带来很大的影响”。
追记钟扬教授两三事:
箱子和牙刷
第一次见钟扬教授,被惊住了,黑红脸庞,壮实的肩膀,实在太不像“教授”了。他的办公室里,特别醒目的是一个卧在办公桌旁的大箱子,许多行李托运标签还没撕掉,洗手台前,牙膏牙刷一应俱全。“我经常要出差,这样最方便啦,”钟教授这样说。
青藏高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热点”地区之一,100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这里的植物资源及其特殊生态环境的研究兴趣有增无减,培养出一支西藏“地方队”尤显重要。十多年前,钟扬主动找到西藏大学:“西藏的研究条件得天独厚,生物学科肯定能够做好。”在复旦大学支持下,他开始在西藏大学从事科研合作,当时并没有任何额外待遇。
“创业”之初,最大的障碍并不是高原反应,而是信心。当钟扬提出“以项目带学科带队伍”时,西藏大学副教授琼次仁和不少老师一样,不相信能做得成,因为那里没人申请过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钟扬什么都没说,他和大家一次次去野外考察。2002年,他指导琼次仁等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未成功。第二年,“西藏大花红景天的居群分布、化学成分变化及地理信息系统研究”项目申报成功,轰动西藏大学。
有一种植物名为拟南芥,实验价值堪比果蝇和小白鼠。寻找特殊的拟南芥材料,成为全球植物学界竞争的方向之一。在钟扬指导下,两位学生许敏和赵宁,利用休息时间,每周末坐公交外加爬山路,爬上4000多米海拔高峰寻访,终于找到一种全新的拟南芥生态型。这一发现即将正式发表,钟扬将其命名为“XZ生态型”,那既是两位年轻人姓的缩写,更是西藏首字母组合,意义非凡。“这是西藏的馈赠,也是大自然的回报。”钟扬这样说。
高山上的雪莲
曾与钟教授聊了很多,印象最深的是这一段话。“雪莲的青藏高原种群相较其他环境优越地区的种群,明显要差得多,但这些矮小的植株竟能耐受干旱、狂风、贫瘠的土壤以及45摄氏度的昼夜温差。生物学上的合理解释是:它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分布最高的植物,就是靠这些一群又一群不起眼的小草,向新的高地一代又一代地缓慢推进……当一个物种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须迎接恶劣环境挑战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些先锋者牺牲个体优势,以换取整个群体乃至物种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先锋者为成功者奠定了基础,它们在生命的高度上应该是一致的。这就是生长于珠穆朗玛峰的高山雪莲给我的人生启示。”
高山雪莲,专业名字叫“鼠麴雪兔子”。1938年,德国探险家希普顿在海拔6300米左右的珠穆朗玛峰南坡采集到这一神奇的物种,将其记载为世界上分布最高的高等植物。今天,对高山雪莲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人类了解全球气候变化与高原生物响应间的关系。为此,钟扬与他的学生、西藏大学同事扎西次仁和拉琼一行,一次次前往珠峰,终于在海拔6100米以上的北坡采集到了宝贵的样品。
曾有人问钟扬,如果不去西藏,留在上海专心搞研究发论文,是否有更多成就。“也许是吧,”他答得坦率,却并不后悔。在复旦大学先进党员报告会上,他就是用这样一段话,来说出自己对高山雪莲的热爱,这何尝不是他的人生缩影?
一首诗,一篇文
“那年8月,我们的考察队沿着泥泞小道穿越羌塘草原。在某天的掌灯时分,一班人马跌跌撞撞来到了班戈、尼玛间一个海拔近5000米的小镇。高原寒夜和连日的奔波使人无暇他顾,我们匆忙间找到了一个家庭旅馆就住下了。半夜,一阵胸闷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急忙唤醒同屋的博士生老王,说‘开点窗吧’。他应声起床。黑暗中,却听‘哐当’一声巨响,一股寒风扑面而来——糟糕,老王把整面窗户从二楼推了下去……”一篇《藏北的窗》,记录的是钟教授的一个平常工作片段。那天采访快结束时,他拿出来给我看,平实的行文,字里行间看得出深深的喜悦与爱,或者还有些“小骄傲”吧。
今天找出来,接着读下去,当时的感动依旧:“窗户掉下去的第二天清晨,队伍重新启程,车开了回头看,熟悉的土墙,挂满经幡的玛尼旗杆,旅馆老板一家子挥舞告别的手臂……那后面,一缕晨光正巧投进洞开的窗口,心头顿时涌起暖意。”
钟教授的学术建树与情感,不仅仅留在西藏,他带着走遍各地采集的种子,为国家种子库的完善奔波;他为上海海滩培植红树林劳心,希望将其作为“献给上海未来的礼物”。如今,红树渐已成林,他却远行。
“世界上有多少玲珑的花儿,出没于雕梁画栋;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罗花,在高山砾石间绽放……”他的藏族学生忘不了,这首藏语诗是老师特别为他朗诵的,祝贺自己完成博士学位论文。那时,一首诗未尽,年轻人已经湿了眼眶。
再一遍,“世界上有多少玲珑的花儿,出没于雕梁画栋;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罗花,在高山砾石间绽放……”
新闻来源:搜狐新闻网站
2017-10-25 上一篇: 预告:9月24日北京校友金秋午餐会 下一篇: 2016年年检报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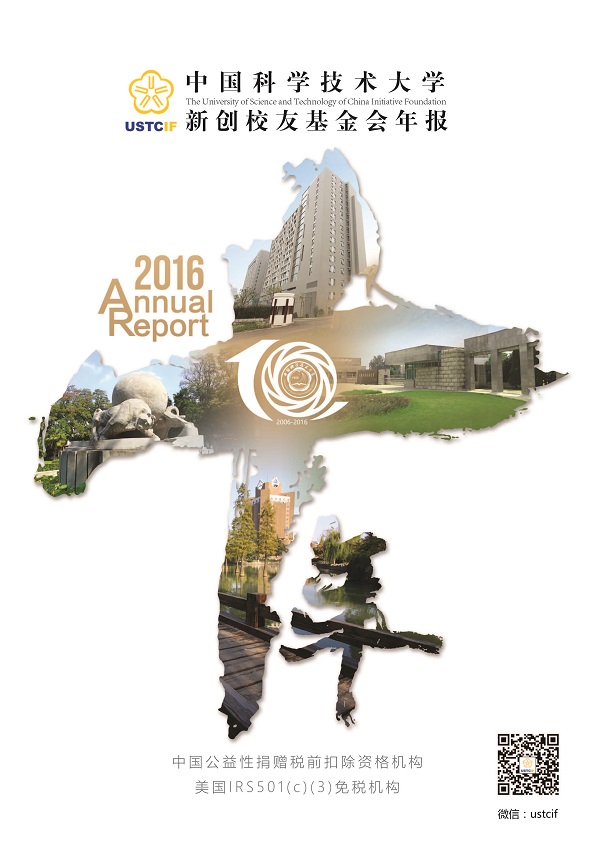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5836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583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