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圆桌讨论 | 见微知著:生命科学与量子物理的碰撞
陈宇翱(主持人):首先我们就基因编辑、干细胞与医学伦理进行交流,王立铭教授一直抛出来这个问题,另外两位老师是什么观点?
章小清:我比较同意王立铭的观点,如果滥用科学技术,后果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因为从目前来说,科学发展的驱动对人类的影响可能太大了。我们所关注的东西,会作为一种驱动力,不管是不是通过基因编辑或者通过其他科学技术,毫无疑问会左右整个发展的过程。一个细胞跟另外一个细胞的差别本来不是很大,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也不是很大,但一个智商150的人和智商50的人,他在整个社会的表现形态上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人是极端聪明的,一个人是极端不聪明的,但是回归到自然属性,你会发现不聪明的人,可能还有很多其他更优秀的优点,我们可能会忽略掉。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够通过对于一个事情的片面理解,去片面地过度追求。但是如果是一件很明确的事情,是本着一种善意、一种治疗、一种不得不去解决的问题,那么我觉得这种技术是应该优先进行推广的,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点思考。
仇子龙:我跟大家多讲一个故事,老百姓可能知道贺建奎的事,你们知不知道2017年美国人跟韩国人,已经在人类细胞里面很完美地修复了一个基因突变,人类胚胎没有生出来,只保存了14天。美国人和韩国人的技术非常好,很完美地把一个先天性心脏病的基因突变修复了。这是2017年发表在国际顶级杂志《自然》上的一篇学术刊文。我去年在韩国听这个做基因编辑的科学家的报告时,我坐在底下从来没有这么震撼。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呢?因为他修复了一个先天性心脏病的基因突变。我觉得特别感慨,之前我们在中山医院,跟中山医院心内科的医生有合作,他们也碰到过这种基因突变的病人,但是目前来说基因编辑并不是最好的和唯一的方法。因为我们可以做产前的基因筛查,这种病是很严重的,一般都是家族性遗传病,都知道父亲得病了,爷爷奶奶有得病的,然后我们根据基因测序,能够找到基因突变,能做产前基因诊断,能做辅助生殖。修基因不是唯一手段,可以做试管婴儿,看哪个受精卵携带基因突变,哪个不携带基因突变,只挑不携带基因突变的,现在上海很多大医院都能实现,这是一个常规技术。一个常规技术能够很好完成的事情,为什么还要做基因编辑?显然他们想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说关于智商的、长得漂亮不漂亮的、或者肌肉强壮不强壮,这些不仅理论可行,实际也可行,有70%以上的可能性修复,以后可能性更大。大家觉得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被社会接受呢?以前当试管婴儿刚出来的时候,并不被接受,宗教认为你凭什么造人,上帝才能造人,后来觉得挺好,可以帮助不孕不育的人生孩子,人类的观念也在变。但是人类什么时候能接受基因编辑健康胚胎?这个是不知道的。大家必须一起来探讨,这是我自己的一些观点。
陈宇翱:说到突变,讨论到近亲结婚容易产生突变,是不是每个基因都很完美之后,一些自然的选择会产生突变来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就是有一些我们可能还探测不到,或者没有办法控制的突变产生,这是一种自然选择?
仇子龙:理论上我们现在所谓的罕见病,就像近亲为什么不能结婚。因为我们每个人确实携带很多隐性的遗传疾病的位点,只要不近亲结婚就没事,机率很低的。比如交通事故,只要你不酒后驾车一般你不会出事,但是你只要开车,你仍然有十万分之一别人来撞你。没关系,我们生活的社会有风险,这个风险可以接受,不用去改变。但是如果是科学上,我是完美主义者,我特别有钱,我的孩子一定要完美。科学家你先帮我把序列测好,告诉我有什么隐性的位点,你把隐性位点修好了,我要一个完美的孩子出来。可不可能呢?当然可能,但是我们会碰到更多的问题,出于科学家的常识,那样肯定是不好的。所谓的突变,就像镰刀形贫血,它好不好?当然现在是不好的,但是在几百年前那就是好事,没有突变,你就要死掉了。现在觉得携带这个基因突变不好,一百年以后谁知道?没有人有这个远见,能看一百年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你过度追求完美,导致一百年以后你的家族比别人更脆弱,你愿意那种事情发生吗?
陈宇翱:我们下一个主题是“生命科学与量子物理的交叉”。我先简单讲一下,之前在墨子沙龙和其他老师也讨论过,在我们看来现在各个领域,当你追本溯源,追究到底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当你去考虑个体的时候,不得不考虑量子效应。现在已经有一些交叉,我先问问看在各位的研究当中,目前有没有到这个程度,或者说已经需要考虑到量子效应吗?
王立铭:这个事我真有一些想法,我估计我们三个可能差不多,生物学研究还没有到这个份上,我觉得归根结底的一个限制是研究手段的限制,有时候只能研究群体效应,一群细胞或者一群个体,或者至少一群分子表现出来的某种行为。在这个时候量子效应可能即便有,也被淹没在噪声里。我倒是相信这事确实存在,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就是薛定谔在1943年的《生命是什么》的演讲。当时1943年的时候,人们还不知道遗传物质是什么,大家只知道遗传,还不知道DNA,更不知道双螺旋,也不知道中心法则。但是他在那本书里有一个章节就在讨论,他觉得遗传物质是什么样,经过了一系列分析,他觉得遗传物质肯定特别小,因为照射伽玛射线它就突变了,他肯定特别小。如果是一个巨大的东西,不可能照一点伽玛射线就突变了,然后藏在细胞内部,又能编码那么多信息。他根据这些蛛丝马迹猜测,决定基因突变的肯定有点量子事件,所有父母生孩子,包括所有细胞分裂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基因的微小变化,这个很可能是一个量子事件。我觉得他这么说,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是量子物理学家。但我觉得他这么说原则上是有道理的,当你讨论到一个分子的行为的时候,在细胞深处复制、分裂的时候,在这个尺度下,我觉得量子现象肯定是没有办法忽略的。我们现在虽然在研究大脑,但是更多的是研究成百上千的一大群的神经细胞,当然我们考虑到单个神经细胞的某一个接触界面上发生了什么具体的事,可能也要考虑到量子效应,但是我们的研究可能离那一步还有很遥远的距离。
仇子龙:我们现在研究的手段非常有限,不是我们不能干,是敌军太狡猾。生命的现象非常复杂,而且坦白地说我认为在逻辑思维的方向,研究生物的不如研究物理和数学的。因为数学和物理世界的逻辑体系可以解释,可以做推理。生物学家说我这个系统很复杂,所以我就不用这个事情。导致我们在分析处理理性体系的推导过程当中,我们没有这个体系。
所以我觉得是手段有限,我希望一百年以后出现聪明人,告诉我们你们研究半天都是瞎搞,我们领域的优秀科学家经常感叹,一辈子皓首穷经也搞不清楚一个生命现象,所以我们期待以后有这种物理级别的,也可能是量子物理,也可能是其他的,真正到生命底层去。量子物理是基本粒子的水平,生命是大分子的水平,大分子现在没有这个理论。大分子水平什么时候有这个理论,我就欢天喜地了。就不用忙半天了,忙于证明那些牛人的理论就可以
章小清: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类似于唯物和唯心。因为我做干细胞,也做神经的、基因编辑的研究。在这里面有时候我们老是想着追根溯源,就是把很多不理解的事情,最后落到物质的基础上。在落的过程当中,是我们逐步探索的过程。其实我想任何东西最后都是可以落的,但是要落到哪个层面,这个是可以选择的。有时候选择在最细最细的层面是好的,因为它是回到事情最本质的层面。有时候可能没有必要,像我们从太空当中看一个一个量子的时候,量子可能就是一个个的星球。在我们看个体的时候,量子其实就是一个个的细胞。我们把一个细胞作为宏观的层面近距离看的时候,一个个量子,可能就是一个个生物大分子。在了解生物大分子的过程当中,就得回到小分子,小分子在回到更细更细的状态再推下去。所以对于不同的事情来讲,我们可能需要追溯的层面不一样。有时候追的过细,就太偏重于西医。有时候太宏观,就太偏重于中医。
所以我想在研究的最高境界,它一定是贯通的,我们从很小的点放大以后,才能把这个事情看得更加透彻。这两者之间结合起来,我想可能不只是在我们讨论的层面上,是在我们后面整个人才培养的模式上。大家知道现在高考,物理化学是可以选择的,现在选物理的人越来越少,因为太难了。考分不高,所以我不如学点其他的。最近从整个教育的层面,现在有很多的措施,鼓励大家选物理。所以我觉得物理要学好,我们可以穿透现象看本质。
陈宇翱:其实量子力学从1900年普朗克提出来以后,大概一百年的时间里基本上还是对宏观的观测,对集体现象的直接运用。一直到最近二三十年,人们才开始操纵单个量子,反过来操纵多个量子,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不一样的计算能力,不一样的手段,其实也是这个方向。
提问:CCR5在免疫学上是趋化因子,它对于抗炎通路、还有细胞迁移都有很大作用。对于艾滋病人,把它去掉了是有好处的,但对于正常人来说,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CCR5对整个机体通路的影响”,我们有这方面研究吗?或者以后在做基因编辑方面的研究时,会不会从通路全盘考虑,而不是说从一个点?
王立铭:这其实是个挺重要的问题,可以从几个层面来说。首先我们知道人群当中有百分之几的人天生CCR5基因缺陷,这群人总体活的还不错,但是近年来有几个报道在说CCR5基因其实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功能,比如说缺陷这个基因,人就更容易得流感,被病毒感染之后,更容易有非常剧烈的反应,健康会受到很大的威胁,它对神经发育也有影响。所以这个基因除了与艾滋病有关之外,肯定还有其他的功能。要把一个人所有细胞里的CCR5基因都破坏掉,肯定会导致一些预想不到的结果,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作为艾滋病患者来说,真正讨论伦理这个词的时候,它有很多内涵,比如宗教伦理、医学伦理、生命伦理等等。我们具体说医学伦理,从医学伦理来说,一个操作对于病人的好处大于坏处,我们就应该可以考虑做。对于艾滋病患者来说,第一我们只换掉他身体内部分细胞的某一个基因,本来也不会影响到神经发育、对其他疾病的抵抗,所以相对来说坏处比较小。好处当然很大,可以帮他治疗艾滋病。在个例的衡量里面,我们做基因编辑肯定有合理性。包括我们用基因编辑的方式治疗其他遗传病,比如刚才子龙讲到先天性心脏病,那可能也是有合理性的,因为带来的好处很大,副作用相对来说可以控制在某些范围之内,就是收益显著大于风险我们就可以做。
真正有问题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把刚才我说的基因治疗的措施往前推一步,直接在健康的人身上修改基因,让这个人可能获取一些本来没有的能力,比如让他天生对艾滋病免疫。这个时候我们必须重新衡量一下收益和风险,收益不太大,因为他本来就没病,相当于让他获得了一些额外的收益,这个收益很难说有没有。因为他可能一辈子不会暴露在任何艾滋风险当中,那他的收益就是零,但是风险是很大的,因为可能破坏了他全身的基因,会导致一些难以预料的疾病,这个时候收益小于风险。这也是为什么如果真有一天修改人类胚胎,引入某些我们想引入的基因变化,需要非常审慎才行。远比在一个病人身上修改一部分身体细胞的基因要审慎的多的多才行,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考虑收益和风险的时候,在这两种情况下考虑的因素是不一样的,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提问:未来在人工智能领域,有没有可能出现一种硅基——可以自我复制的类似于DNA的技术,使未来的人工智能可以像人类一样自我复制下去?
章小清:我个人感觉,人工智能的复制在程序方面、智能方面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但是从生物学方面的复制,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所谓的智能,最后必须要通过物质的载体进行承载,人工智能的载体承载更多的是智能性、进化的属性,是一种复制性或者学习的能力,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它整个的继承,必须停留在物质的基础之上,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东西创造这种物质,但是这种所谓的复制,跟我们人类的复制,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仇子龙:我推荐你看一本书——《生命3.0》,你可以当成科幻小说读。它讲了一个硅基的生命。我同意章老师的意见。
提问:一个11岁的男孩儿发生车祸,动了颅脑手术以后导致他的嗅觉完全丧失。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基因编辑或者干细胞注入等手段,使他的嗅觉重新恢复?
章小清:在这个问题上目前靠的比较近的科学研究,确实是干细胞领域。因为我们嗅觉的感知在鼻腔最上面,神经是通过颅骨上很多的小孔,传到我们脑子里。受外伤的时候正好把这个神经弄断了,所以闻不到味道。嗅觉的丧失虽然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困扰,但是它一定不属于干细胞临床研究的首选病例。因为临床研究从伦理角度来讲,它一定是目前来说最迫切的,目前没有其他任何办法,而且给病人带来生死攸关影响的研究。目前来说不管我们国家还是全球,我都没有听说过关于嗅神经再生的临床研究。恐怕还要再等一段时间,等到干细胞真正走上临床以后,有可能这部分病例会被大家所纳进来,这是我的一种了解。
仇子龙:我建议孩子可以到华山医院脑外科拍一下脑部核磁共振,我们经常接触神经外科的医生,有各种各样很奇怪的病例。因为嗅觉在人体里面,有可能并不是实质性的损坏,而是大脑皮层某些区域的损坏,导致嗅觉不能产生。所以我建议仔细给他测嗅觉,看看核磁共振,看一下大脑整个嗅觉结构有没有变化(当然这是神经外科医生的范畴)。
提问:我国人类资源办公室的流程,有些工作流程过于严苛,是否会影响我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之间的国际合作?
仇子龙:之前因为有过这种例子,就是我们中国人本来说好的,是中国人跟国外科学家的合作,我们都跟国外的同行有很多合作,但是为什么出了这个问题,是因为曾经有一个合作,他违反了当初的规定,然后国外拿着我们的数据就去发表了,完全违反了我们当初的约定,弄的我们很郁闷。所以科技部有这么一个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管理也很严苛。但是目前我相信对于正规的科研合作没有明显的负面作用,因为有什么实验真正是美国人能做我们不能做吗?其实很少,没有的。所以我们追求的是平等姿态的合作,对于我们来说他们的管理,我觉得严格也好,没有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科研交流。
章小清:目前来说我们还是偏薄弱一点,因为很多的遗传信息作为公共数据库的形式,都是在网上公布的,全球所有的科学家都可以免费接触。所以在这个里面,相对来说是公平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我们也要建立自己的公共数据库,这个其实类似于有点卡脖子技术的意思,它也不是一个技术,它只是一个平台。在目前来说如果我们过度依赖于国外的公共数据库,有可能在某一天他不让你使用的时候,会对我们整个科学研究带来无比巨大的影响。所以在这里面是双方的,目前从科学角度来讲是公平的,但是从平台和管理的角度来讲,需要每一个国家建立自己比较有特色的,或者是自己能够掌控的公共数据资源,这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利的。
提问:基因编辑治疗的疗效会不会遗传到下一代?
仇子龙:目前的基因疗法都是针对本人的,不会遗传到下一代。遗传到下一代的是精子和卵子,我们现在所有的操作都是在血液里面、全身的、大脑等等,不涉及生殖细胞,所以不会影响他的下一代。
提问:在基因编辑疗法成熟之后,它的成本是否会降低?是否会利于普通的罕见病家庭更好地接受治疗?
仇子龙:很尴尬地回答一下这个问题,现在美国上市的基因疗法药物,已经上市的意思就是有个价格可以卖了,它的价格是天价,几十万美元算便宜的。我说的那个刚出的药物,它的定价是一百万美元。咱们这么看,第一,它真那么贵吗,药物公司是不是要赚钱?第二,药物公司说那么贵不是没有道理的,我花了很多钱研发。我这么来看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医疗市场的问题,在美国医疗市场,有保险公司买一部分单,它是有医保的。问一个普通美国老百姓要一百万美元,他也没有啊,他为什么能出的起这个钱呢?去年Biogen公司SMA的药物卖了几亿美元,美国一般家庭拿不出几十万美元给这个孩子治病的,他肯定有保险,而且还cover的不少。所以换句话说,它在价格上没有比传统的药物更便宜,但是它治的所有病都是传统医药治不了的,没有其他药物可以替代。但是收多少钱,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需要更多专家去研究,不是我本人的领域,我没法多说。
关于墨子沙龙
墨子沙龙是2016年潘建伟院士提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研究院主办的科普论坛。经费由中国科大新创校友基金会捐赠资助。沙龙的科普对象范围从对科学有浓厚兴趣的中学生到成年人,旨在通过科普讲坛、和科学家面对面的方式对他们进行专业的科学启蒙。以上海为中心向全国发散,通过讲座、视频、网络公开课、科普订阅号等多种方式开展科普活动。
墨子在战国时期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是我们中国最早的科学家。《墨经》中有关于力、力系的平衡和杠杆、斜面等简单机械的论述;记载了关于小孔成象和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成象的观察研究,首先提出了朴素的时间(“久”,即宙)和空间(“宇”)的概念。墨子沙龙以墨子命名就是希望传承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精神,振兴中国现代科技,鼓励青少年走上科研探索之路。
2019-05-10 上一篇: 【通知】探索宇宙中人类的第二个家报名 下一篇: 【漫画】 你看的每一篇Nature论文,都是这样出炉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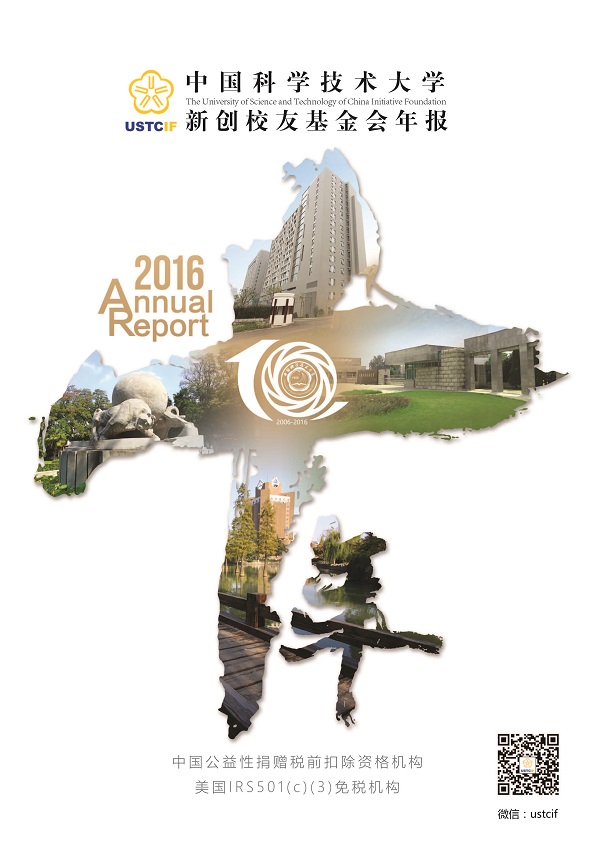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5836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583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