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夜雨(续)
(五)青锋过处万骨枯
从接待新生开始,就会有热心的学长时常过来和我们聊天,科大的辉煌历史,睥睨天下的黄金时代,旧黄山路的风味小吃,教授师长的掌故传奇,海阔天空,无有不及。于是得知很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其中便有江湖上传闻已久的四大名捕。
都上过张鄂堂老师的课很久了才想起张老师早些时候也是用一招“兰花拂穴手”打得傲气十足的科大学子丢盔弃甲的冷血杀手。刚进科大的学生都是各中学的佼佼者,意气风发,志得意满,自以为全中国老子第一,期中考试过后你试试看,一刀下去总有十数人落马,当时就让你知道什么叫中国科大,什么叫好好看书。我上张先生的课的时候,他已经杀性大减,立地成佛了,许是人上了些年纪,厌倦了这江湖恩怨,手下也就温柔多了。在张先生手下捞了88的分数,勉强过得去,不过据说还是有几个人被张先生大象稀形的刀锋无意砍伤。
倪其道老师教化学,我上高中的时候化学学得最好,高考丢了两分愣是郁闷了半个月。到了大学以为化学嘛,不过是勾勾兑兑,拿几个方程式折腾折腾。上了倪先生的课,知道全然不是这么回事,不但上课需要把耳朵立得跟狗一样,还得练就边听边速记的本事。倪先生内外横练功夫登峰造极,敦厚仁慈,说话很慢,和他的考卷杀气腾腾的样子完全不搭边。考试前,我们也曾小心翼翼地去套磁,倪先生立马横刀,一柄震远流星锤使得滴水不漏:孤魂野鬼,不得相犯,佛手拈画,亦可伤人。那时候的学生也老实,一看捞不到便宜,马上乖乖地去看书。那次考试,或死或伤,哀鸿遍野,我得了好像76分,自觉得逃过了鬼门关,一问才知道是开了根号。倒。
西区宿舍楼
今非昔比的西区,图片来自中国科大文化网
量子力学的难度和金庸先生笔下的“易筋经”差不多,功力不深的人就是练了,也容易走火入魔。当时给我们上量子力学的是朱栋培老师, 朱老师讲课很为浅显,让我受益非浅,我听得兴高采烈自觉开窍,但是助教老师却说了句:“朱老师现在是真忙啊,课备得没有以前那么细了。”可以想象朱老师刚上讲台的时候何等一丝不苟,呕尽心血。其中考试的时候可以查书,可以看笔记,可以查资料,除了互相讨论外什么都可以,结果全班58个人超过30个不及格。95级师弟讲了一个关于朱老师的故事,朱老师上他们课的时候,问大家是不是最后考试的时候就出很简单的题目全部放过呢?大家做拥戴状,朱老师在黑板上疾书四个大字:“天地良心”,说道:“需知世上还有这四个字在啊。”后来朱老师因行政工作太忙辞去教学岗位,这是个无法弥补的遗憾。
李百浩老师杀人的绝招是“迎风一刀斩”,其惨烈程度代代相传,令人闻风丧胆。据说有一回,改卷子先不打分,数出全班考得最差的18份试卷--“你们不及格了。”,“李十八”从此威震科大所有门派。李老师的课条分理析,脉络分明,讲的人壮心不已,听的人风云际会。李老师是我见到的唯一一个亲自批改所有作业的老师,而且会在作业本上写上错误的原因。拿到这样的作业本,谁都会脸上发烧,再也不敢打抄作业的鬼主意。
上我们数理方程的是王仁川老师,据说是研究相对论的大家。王老师的课犹如汗血宝马,一日千里,让我们大呼难熬。因为他没有指定教材,完全是按照自己的讲义,我们连滚带爬,也只能看见先生在前面缥缥缈缈的身影,大约上了一个半月,有一堂课上,王老师突然停下来问:你们是不是听不懂?大多数同学猛点其头,王老师半天没有说话,后来说:我前一次上课是给8X级的同学上,所以按照他们的进度来赶。你们真的大不如从前的学生了,算了,我们还是按照科大出的《数理方程》来上吧。王先生轻轻叹了口气,那次课很早就下课了,我们都没有说话,默默的下课,回去吃饭,脸色好多天没恢复过来:我们不再是黄金一代,让老师和自己都失望了。大概过了两年,突然听说王先生病逝,这个消息呛得我半天缓不过神来,王先生矍铄清健,怎么突然就仙去了呢?合肥的天空阴沉潮湿,雨水垂翼在这灰暗的城市,我和同学赶到合肥殡仪馆,先生果然安静的躺着,再也不会为科大的学生伤心和失望了,我恭恭敬敬地给先生鞠躬,陡然鼻子一酸,哭了,这种混合着愧疚和自责的心情一直藏在我的灵魂深处,在我消沉退缩的时候,我会想起它,想起先生的一声叹息。尘归尘,土归土,愿先生永安他的灵魂。
还有许多这样可敬可爱的老师,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不懂得一团和气,不懂得蜿蜒曲折,正是他们,为科大的历史写下光辉的篇章,正是他们,是科大的精神之所在。现在居然有上课接听电话的老师,我 为他感到羞耻。
(六)鸿雁长飞光不度
我们生于70年代,成长于80年代,独立于90年代,中西文化的碰撞,改革开放的阵痛,深刻的信仰危机,所以我们是复杂和困惑的一代。
刚到科大的时候,西区的澡堂在现在水房的对面,只是两个又黑又小的房间,屋顶上挂着晦暗不明的白织灯,颇有些象法西斯的集中营。那时候的学生都很自觉,尽量动作迅速,手法简练,多留时间给后面的同学,好像是95年,就修新的澡堂了,我不是自虐的人,所以这当然是一个可爱的进步。
站在黄山路上,望着十几米宽的道路和花团锦簇,我时常会感到眩晕。10年了,我记忆里黄山路上漆黑的雨夜也开始慢慢褪色。94年的荒山路大概3米多宽,坑坑洼洼的到处都是坑,隔很远才间或有一个快睡着的路灯。靠近金寨路的地方有不少饭馆,靠近科大的地方九比较荒凉了。路两边是低矮的瓦房,房前长着参差不齐的杂草,到了冬天特别萧杀,特别是大雨如注的时候,雨水敲打着雨蓬,走在着凄凉而寂静的雨巷,有时候会有一点心惊肉跳。路的中段有一个报警亭,不过从来没有看见过人,除了偶尔有手扶式拖拉机驶过,这里看不到任何现代繁华的气息。我们的实验课在东区,一做就是九十点钟,三两个同学走在路上,听着自己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所以我记忆里的黄山路永远是一幅黑白照片,保留着拓荒者最后的一点痕迹。
到底是哪一年开始,寝食全部装上了电话,我已经不太能记得。对于初到的我们,能接到一个电话是多让人向往的事情,整个四号楼就传达室一部电话,传达室的大爷用对讲系统通知要接电话的同学,于是他用百米短跑的速度自豪地跑下楼区,踩得楼梯咚咚直响。遇到节日或别的特殊的时候,传达室的电话热得吓人,根本打不通,我们只好到公用电话亭区打,电话亭的位置在现在西区理发室的地方,很窄小,不过确实我们心中最温暖的地方,交上押金,排个号,等着那个有雀斑的姑娘叫自己的号。我记得94年的冬天,我曾穿过厚厚的雪幕,用失态的兴奋对着电话听筒大喊:妈,下雪了,真的下雪了耶!!。
象堂主这样的第一批拓荒者,西区图书馆成了他们无法释怀的遗憾,我们进校的时候,图书馆已经巍然地矗立起来,似乎总有两个人拿着榔头叮当叮当地敲打什么。黄吉虎老师笑眯眯地说:应该快了,最多再过一年就能用了。那时候图书馆是修起来了,但还没有装修,建筑队的人已经撤走,临时的篱笆工棚却还在,围绕着工棚是一些绿油油的瓜棚豆架,我甚至记得靠近路边的地方垂着两个硕大的丝瓜,军训那会我们还罪恶地打过它的主意。每次放假回家,我们都会望着阒静无人的图书馆感叹一回:不是说一年就能用的么?那种幽怨的神态和祥林嫂也没多大区别。40年校庆的时候,图书馆终于全面竣工,底楼的自习室成了我最常去的地方,我喜欢它舒服的木头桌椅,我喜欢它墙上的字画,(其中就有朱栋培老师的“极难不难”)我喜欢一抬头,看见许多聚精会神的脑袋,我喜欢听轻轻翻动书页的声音。我在那里面度过了考托福和考GRE的疯狂岁月,它成为我记忆里永远的天堂。
(七)十载烟柳太匆匆
刚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开设了计算机课程,当时14寸的单色显示器还大行其道,486的彩色显示器只有老师才能用,我们只能趁老师转身或不在的时候怯怯地用手碰上一碰,生怕哪个按键就此失灵自己担当不起。95年初,我和另外三个同学一起投入巨资(8000多人民币)买了一台电脑,当时的顶级配置今天看来不过是2000块钱的破烂,不过对于当时的我们,这已经是科学最崇高的展现了。计算机刚买回来的那个晚上,我们小小的寝食挤满了人,比新媳妇过门还要热闹,当晚是我的机时,我玩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游戏《仙剑奇侠传》,无穷多热情的狗头军师象蚕茧一样把我层层包裹,大家为游戏玩法争得面红耳赤,几乎要上演全武行,我则象个惶恐的木偶,看看这边,又看看那边,最后忠实地执行辩论得胜方的意见,不过很多时候是立马被小鬼灭掉。按照安排,每个星期我有两个晚上的机时,不过我再也没有时间靠近它,所有的时间都被功课和自习占据了,毕业的时候,我甚至都没看到它的遗容,它就被折价卖掉,我分到了300块钱。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同样是孤独的一代,89年以后,科大的学生活动日渐冷落,也很少发生校领导坐在学生中间摆谈家常的事情,除了上课,别的时间几乎见不到老师,我们象孤独的孩子,茫然地寻找着方向。大多数同学也没有钱买电脑,我们唯一的群体爱好就是打扑克,周末的时候,被烦人的作业折腾了一个星期,聚众赌博蔚然成风,不过也就一个晚上,第二天又要早早起来窝到自习室去。我们非常团结,自己组织班级足球赛,跑到科学岛上去参观,甚至还安排同学轮流照顾我们系一个瘫痪了的老教授的生活。我们真诚地互相帮助,兄弟般的互相学习,我们刚吵了嘴转眼又勾肩搭背地搂在一起,我们聊美丽的家乡,聊想象中的未来,有时候会天真地以为我们中间将出现第一个诺贝尔奖。我和同寝室浙江的兄弟一起制定要在科大五年里达到的目标,要在当年的班级里取得什么样的名次,我们甚至还阴谋筹划怎么样当上班里的班长和团支书。当时我们是何等的向上,何等的乐观,何等的兴奋,仿佛一片广阔的让我们自由驰骋的大地正展现在面前,正等待着我们在上面泼墨作画,描绘我们在科大的明天。有一天,激烈争辩了地域对科大的影响后,浙江同学说:我将来要回来做科大的校长,要把科大搬回北京去,要让科大成为超一流的研究性大学,我说:好啊,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会回来帮你。校园里的树木徒然增加了许多年轮,这位同学在yale早就拿到了博士学位,现在到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做博士后,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我们纯真的梦想和年少时的诺言,记得那个我们都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班是最团结的,我们亲如一家人,所以才会在送别的火车开动的时候,那么多转过身去悄悄红了的眼睛。
一个又一个晚上,雪白的灯光,窗外呼啸的北风,堆积案头的书本,几乎闪回在我本科回忆的每一个片断。尽管当时的学风已经很难跟八十年代相比,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旧是充实和奋进的几年。为了抢得好的座位,不得不七点钟起床拎着馒头边走边吃,有时候头天晚上就把作业本放在座位上,不过这种做法招到批判以后,就很少人用书本占座了,我们班只有两个宝贝女生,我们会自觉把最好得两个座位留给她们,班级里有什么事,班长总不忘交代一句:“别忘了三号搂啊。”合肥这个小城很安静,没有灯红酒绿的诱惑,特别能静下心来,下午一两点钟到教室,一屁股就坐到五六点钟,站起身来,看操场边如血残阳下高高的芦苇荡,别有苍凉的美。平时稍微好一点,六点多还能找到座位,到考前一两个月,座位紧张得不行,不过没有人会争座位到打架,三教的座位都是三个人的长凳,可以找只坐了一个人的这种位置,安静的坐下去,原来坐的人也自自然然地挪一挪,甚至用不着谢谢。大概是2000年的时候,期末考试前的一个月,晚上七点多我到教室上自习,居然每个教室都空荡荡的只有五六个人,我的失落和难过是难于用语言表达,科大弥足珍贵的一些东西,也许永远地失去了。“中国之大,唯有科大才能容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科大还在,书桌旁边却已空空如也。
(八)欲以热血荐轩辕
比我们老一些的科大人总是会怀念很多年以前的民主气氛和热血丹心。那时候的科大人,豪气干云,热血彭湃,家事国事天下事,每到激越处,颇有慷慨赴死的气势。经过几次政治事件的整顿,科大的声音沉默了,学生社团越来越少,硕果仅存的不过惨淡经营,这不是科大的责任,因为我们一起面临着信仰真空的可怕?危机。
男生没有几个不爱看足球的,爱到如痴如狂,爱到不能自拔,大至世界杯,欧锦赛,小到国内的甲极联赛,无不照单全收,特别是中国队冲击亚洲杯和世界杯的所有比赛,更是万人空巷,嗟叹声,叫好声,遥遥相应,无比壮观。?一次又一次的失利,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后来变成了绝望,但还是爱,爱到故作冷漠,爱到遍体鳞伤。97年在天津举办了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那天晚上是自习室的恶梦,电视机前万头攒动,自习室里凄凄切切。每一个扣杀,每一次得分,都迎来我们由衷的欢呼,当王涛最后一板搞死对手,难抑激动地躺倒在地上,太重的历史和过多的屈辱反衬出来的自豪象火山一样爆发了,整个西区顿时阴风惨惨,鬼哭狼嚎,大家不遗余力地跳啊,笑啊,围着楼梯疯狂地窜来窜去,二号楼开始有人烧被子,然后是啤酒瓶亲吻大地的惨叫,接下来就是规模浩大的泼水比赛,那些上晚自习回来的同学,冷不丁头上醍醐灌顶,如落汤鸡,幸灾乐祸的同学从楼上探出头去,放肆的大笑,更上层楼的同学于是狠命一盆,笑声嘎然而止,不过那时候没有人会生气,多漂亮的胜利啊,这才是中国人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到了晚上12点多,我们还在和五号楼的同学遥相呼应,不过都是音节简单的咏叹调:啊~~~~,哦~~~~~。那个晚上是我最刻骨铭心的快乐,后来女排多年以后再次问鼎冠军,我一点都不激动,也许是我老了,也许是这种激动需要群体的传染而更加动人。
99年的5月,天气已经开始闷热,毕业前心照不宣的伤感气息还没有过分蔓延,不过确实是比较放松了,大家不怎么去上自习,聊天,串门,打扑克,看电视,就要仓惶离去了,让我们醉生梦死一回吧,以后,天长水阔,我们将流落四方。8号那天下午从教室回来,听到将要去签证的几个同学大声嚷嚷,忙飞跑的过去,就听到了三个普通中国人的死讯。我从来不认识他们,也没有听说过他们,他们只是在炮火纷飞的国家里做着一个平凡的记者,但是,美国精确无比的飞弹却很意外的就打中了他们。在睡梦中,三个灵魂永远离去。那天晚上,在电视里确证了同胞在南斯拉夫使馆遇难的消息,还播出了北京高校学生示威的画面,至今还能清晰的记得当时那些愤怒的脸和握紧的拳头。空气异常紧张,仿佛酝酿着暴雨,夜里,西区的草地上出现了蜡烛和小白花,有同学每个寝室通知说明天游行去,大家都不说话,默默地想自己的心事。第二天,我因为一点事情耽误了,回到寝室的时候游行队伍已经开拔,于是骑车到三孝口等,我想那应该是必经之地,不过没有等到,他们走了另外一条道路。我和一个同学跟在安徽大学的队伍后面,我的声音很弱小,但合起来,就形成一股强大的洪流,潜入每个路人的耳里,产生揪心的回响。后来,在电视上看到了烈士的家属,哭肿的眼睛,母亲花白的头发,还有儿子嫩稚迷惘的脸庞,我再次感到揪心的疼痛。我们在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的颂歌中长大,无比深沉的爱着我们脚下的土地,但是,我们却连三个脆弱的生命都无法保护,正如那些在八国联军的铁蹄下象野草一般被践踏了的民众,还有在那场浩劫中无数屈死的灵魂,他们在天国里睁大了愤怒的眼睛,寻找着正义,公理的所在。谁,来挑起这个历史沉重的负载?2000年的5月8号晚上,58事件一周年,我和几个网友站在西区的旗杆前面,白蜡烛,白花,祭奠因时光而泛白的记忆。江水依旧向前,殷红的血色已经被冲淡了,那一幕悲怆将被载入历史,路正长,夜也正长,前面泊着些 微茫的希望,耳边却一直回响着那首《亚细亚的孤儿》: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香港回归,澳门回归,毒油事件,烟草学院学位证事件,世纪交叠,太多的欢乐和痛苦,慈祥的师长,不要说我们冲动鲁莽,“为什么我的眼里满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多少年后,当我们被无情的时光打磨得毫无棱角,四平八稳,我们会怀念年轻时单纯强烈的爱恨,年轻时九死不悔的执着。
(九)临海犹望旧时月
这几天的心情颇有些不佳,一个小姑娘说:你真的很爽啊,闲得无事居然在茶馆发飙。她不过是无意的调侃,我却只能苦笑,往事湿淋淋地从记忆里打捞出来,无比遥远又无比清晰,她已经很难理解这其中悲喜交集的轮回。我是上研究生阶段才进实验室的,所以一直到本科毕业前,我都不知道BBS是什么样子,当时安大的BBS还没有关闭,很多同学在那里闯出了点名头,不过后来有安大的朋友对我说:940X的人真烂,这句话让我倍觉耻辱。99年9月,我第一次爬上了瀚海星云,那时的瀚海是PBBS系统,从功能上来说比FBBS弱了一些,科大人却乐在其中,对它宠爱有加。有外校的同学登上来,半天找不着北,发泄一通骂曰烂系统,该拿去喂狗。科大人总有人跳将出来,自豪地表白一番,说这是大陆唯一的PBBS系统,老少皆宜,童叟无欺,味道真是不错云云。后来瀚海还是改成了FBBS系统,当时哭声震天,各种祭文推陈出新,场面甚为感人。PBBS代表了真诚和热情,折射了网络积极美好的一面,对它的挽留和怀念其实是缅怀那个时代的美好光点。
初入翰海,我被一种自我折磨的痛苦纠缠着,我成天呆在聊天室里,意志消沉地自言自语,就象跟女儿讲长袜子皮皮的林格伦,或者孟庭苇歌里那个对饼干说话的人。有一天晚上,我在BBS的信箱里收到了一封信,发信人写到:我觉得你好象不快乐。相信我,一切都会还起来的。是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那种温暖的感觉多年以后还久久不散,也许要持续到未知的明天去。那时候我的导师刚好到美国去做访问学者,带我的是一个博士,不折不扣的好好先生,每每我问他是否需要我做什么事,他就刷一下红了脸,欠了我钱似的忙不迭说:不要,不要,你专心上网,专心上网。于是,我逍遥自在地在瀚海里整整泡了两年,聊天,写小说,和有趣的朋友聚会,参加网络公益活动,并由此结识了许多肝胆相照的朋友,我会永远怀念那时候瀚海的真诚和快乐,小小的网络犹如窗外的四季层次分明地更迭,欢乐和忧伤如潮水涌起又退下,关于王小波和苏轼的热烈争论,关于ID后面的神秘猜测,温馨美好的网络文字,还有通过网络组织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时光流星一样划过几个整合的圆弧,终点又回到起点,还是这网络,这江湖,仗剑关西的网上侠客人迹杳杳,现在都是陌生和新鲜的脸,纠集着饭局,传播着八卦,我平静注视着BBS慢慢变成集体娱乐场,想起PBBS时代的刀光剑影,封站,封版,查处ID,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后来,我基本上彻底离开了网络,这个曾给予我鼓励,给予我温情的虚幻世界,人活着有很多种姿态,窗外有着更精彩的世界,我们有着更重要的责任,寻找所应寻找的,追求所应追求的,这才是生命本来的关系。许多生动的脸,许多美好的往事,只对我有着特别的意义,那是无法分享的欢乐,我想用以前写过的一段话结束关于往昔的瀚海田园牧歌似的追忆吧:朋友曾说我是过于感性的人,适合坐西窗绣鸳鸯。在我的记忆里,狗熊是个理性更甚的人,不过如果这个世界都是面目相似的人,也就很无趣了。我和狗熊是完全不同的人,追求着相异的幸福和形式,我们将独自度过自己的旅程和岁月。
大四对我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年,那一年选专业的时候,我选择了等离子体,这是一门还相对新兴的学科,全国的大学似乎也只有科大有这个专业,在这条人迹罕至的小路上踏破荆棘,那该是多么壮烈和激动人心啊。不过我终于还是放弃了,学不太懂,以前上过的四大力学也考的惨不忍睹,我不得不残酷的解剖自己曾经的梦想,结论是可怕的,我看着从上大学的第一天就竖立起来的神邸轰然倒塌,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如何惊心动魄的混乱。我茫然地问同寝室浙江的兄弟:我真的该放弃吗?我真的该放弃吗?我抱着他哭了,他只能轻轻排我的肩膀:无论选什么方向,对社会有用就行,还是要符合自己的兴趣。在内心激烈的战争中,现实中的我败下阵来,年轻只有一次,我实在输不起啊。今天看来,这次选择也许是正确的,我希望将来去做电路芯片,幻想有那么一天,中国所有的电路板上的芯片都Made In China,这条路很不好走,不过走的人多了,自然会成为路。
(十)一切刹那皆芳华月
不知道为什么,我所有印象鲜明的回忆都和本科岁月有关,也许是因为一起淋过的电影散场后的大雨,也许是一起听过的校园深处的叹息,也许是一起憧憬过的责任和梦想。多么庆幸啊,我生于70年代,并选择了科大作为年轻时的精神家园,所以领照了理想主义灿烂的余晖,所以在这纷乱的时代还能保留自由的呼吸。
14年前的那场手术在我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头坚持不懈的疼了14年了,敏感,失眠,怕一切声音,怕刺眼的阳光,经常大汗淋漓地在梦里醒来。有时感觉力不从心,几乎就不想起来,伤心过,绝望过,但还是咬着牙关挺过来了。别人都用“精神抖擞”来形容我,生活和我开了一个多大的玩笑啊。1996年和2003年炎热的夏天,我挥汗如雨的学习过;2004年那个记忆里最寒冷的冬天,大年初三我在实验室手脚冰凉地工作过,我可以骄傲地说我尽最大限度地珍惜了我的黄金岁月,尽管已经留下了太多遗憾。我在给朋友的信里说:多羡慕那些健康奔跑的少年,可惜很多甜美的青春却在网络上,在游戏厅里,在发呆中白白流失了,我替他们惋惜,我们完全可以过不同的生活,如果我们愿意,确实可以作成多少事情.....?。还记得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吗:当一个人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应该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应为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的话也许听起来有点可笑,可是,你能更好地告诉我生命的意义吗?
十年了,芳华园里经常流淌着歌声,理化大楼巍峨地刺破苍穹,总是漏雨的七个洞灰飞烟灭,风穿过西区的时候也不再象当年那么流畅和随意,回忆中的许多具体的形体都消溶在往昔的昏暗中了,只留下来各式的"符号",可能是某种香味,可能是某个背影,甚至可能是某种颜色。而这些"符号"却往往与原物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当我将水冲入茶杯,看着一朵朵干皱的菊花慢慢舒展开来,同时嗅到那清苦的香味时,这香味便仿佛一道闪光似的划破往昔的黑夜,照亮了记忆中的某些片断。
量子信息,纳米技术如火如荼的蓬勃着,数学系和物理系却衰败了,起码表面上如此,人才象黄土高原得泥沙一样流失,多少年以后,我们可能会读到这样的字句:它们在科大的历史上,犹如历史长河中的巴比伦文明,流星一样划过惊鸿一现的光芒,然后就永远的衰落了,只留下无法考证的神秘回忆......杨福家在科大的211评审会上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不应单单注意科学,还应注意技术,即怎么对我们国家的经济有更直接的推动。像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它经常非常自豪地说,对美国国防和高技术企业有影响的先驱的技术,首先在它那里发源。作为一个普通的学生,我无法对科大工科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也无法对科大的战略定位有过多的评价,我只能多么殷切地希望她一路走好,希望当科大百年校庆,我们再聚首科大的时候,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国家所有的重大工程,都有科大人的贡献,科大工程学院为国家贡献了数量众多的院士,它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最低调的巨人。
科大会继续发展,继续进步,科大人自由民主的精神向度和洁白朴素的生活作风会继续传承,象三教前那株每个冬天都准时暗香浮动的腊梅,不过我们也遗失了很多值得宝贵的东西,校园里被踩坏的草坪,图书馆被撕破的书页,冷落已久的自习室,无人响应的公益活动……。前两天和朋友说到中国的持久发展必然需要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回归,对此我们乐观并坚信无疑,正如科大在经历了那么多年的风雨依然奔腾不息,已有的需要代代相传,失去的我们也必将寻找回来。望着夜色中灯火辉煌的三教,我仿佛看到过去的影子,穿过历史的界限,科大将永远散发动人的芬芳,这是毕业生共同的信念。
星月皎洁,明河在天,还是一样的暮色冥冥,还是一样的青春年少,但是,就十年了。西伯利亚沉淀为历史,我记忆中的西区也日渐模糊。再过一个多月,我也将飞走,离开这个留下了脚印的地方,不过我想我以后的岁月必将和科大保持某种温暖的联系,那是无法割断的血脉之源。合肥的夜雨敲打着窗台,昨日却无法重现,让我以喜爱的一首歌来结束全文吧,大佑的《闪亮的日子》。木吉他伴奏,朴素的声音,用很简陋的装置录成, 正如我所经历过的科大十年,粗砺,简单,却让人终身怀念。
我爱你,科大,我一生会为你骄傲。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我想不出更好的词汇了。
2013-06-15 上一篇: 十年夜雨 下一篇: 2013年朝鲜核爆炸,中国科大不高兴?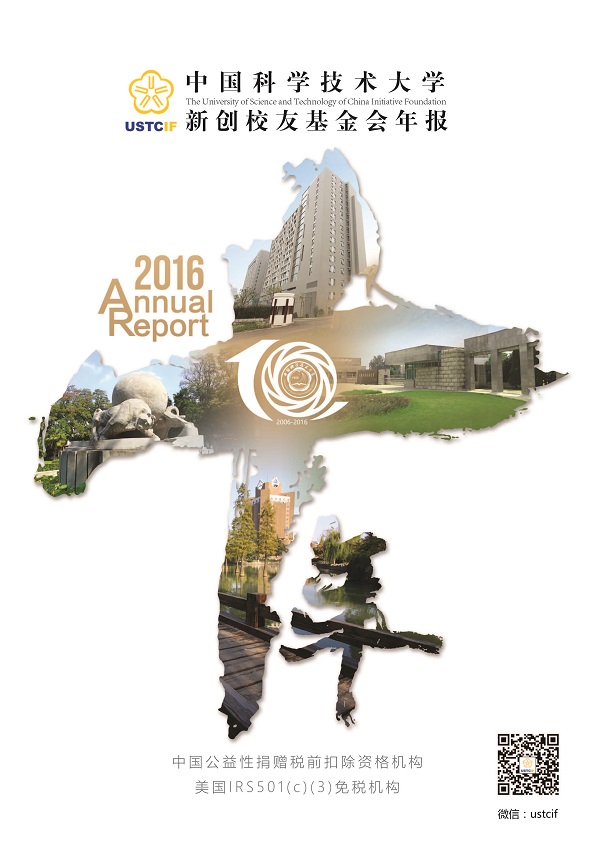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5836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583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