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访谈】 科研的“三严”传统需代代传承
李曙光院士访谈录
陈雪纯 访谈整理
访谈整理者按 李曙光,地球化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1941年出生在陕西咸阳,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科大)地球化学系并留校担任教员,上世纪70年代参与国家铁矿会战,80年代初访问MIT系统学习同位素年代学,长期致力于大陆碰撞造山带化学地球动力学研究,2011年以后致力于金属同位素示踪深部碳循环研究。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5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2010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访谈主要介绍了缘结地球化学专业的前因后果、困难时期科大朴素的学习生活,以及毕业留校工作和后来访美研学过程中的大小境遇。受访人的求学与科研经历反映了一个时代科研环境变迁的缩影。
受访人 李曙光
访谈及整理人 陈雪纯
时间 2018年5月21日
地点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专家楼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图1 李曙光院士(2018年5月21日张雲涵摄)
一 结缘地化,来之安之
陈雪纯(以下简称陈):李院士,我们在研究近几十年来中国科研环境的变迁,想请您从自身经历出发谈谈相关情况。就从您当年为什么选择报考科大,又为什么选择了地球化学这样一个交叉学科谈起,好不好?
李曙光(以下简称李):好的。我中学的理想是学航空,我在中学玩了五年航模,对航空有兴趣。本来想考北航,那时我中学校长说:“新成立了一个中国科大,是中国科学院办的,你成绩好,为什么不去考科大呢?”我说我想学航空,校长说科大有力学系,钱学森是系主任。我一听,那很好,就填了科大为第一个志愿。
但是那时候,中科大在天津招生,要求一律专业服从分配。我想让招生人员了解我的兴趣从而能分配到力学系,后面几个志愿都写了和航空相关的校系,第二志愿是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然后是哈尔滨工业大学航空系、西北大学航空系、南京航空学院,后面志愿全写的航空,想让招生人员看清楚我是喜欢航空的,结果招生人员没理我这茬,把我分到了地化。
我是在报到当天才知道分到了地化,当时就蒙了。地化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反正是搞地球的呗。本想上天,结果入地了,因此头一天晚上没睡好觉。当晚想了两个事情,第一,我是预备党员,1960年中学毕业时,6月入了党,理应服从国家分配,这点觉悟是有的。国家办了地球化学专业这么一个交叉学科,一个边缘学科,说明国家是急需的,所以从大的原则上讲,我作为一个预备党员要服从分配。另外一件事就是想到我为何喜欢航空呢,是因为自己搞航模,看了书、玩得多,产生了兴趣。地球化学这个东西我没兴趣,可能是不了解,我了解之后就未必没兴趣。既然国家需要,我就试着了解它,没准会产生新的兴趣。就那么一个晚上我想通了,就是服从分配,努力了解它。
陈:进入科大地球化学专业之后,您对这个专业有什么样的认识?
李:后来上学发现地质科学课程描述性很多,严格的数学公式很少。不仅我这么感觉,比我们高一届的1959级同学他们也这么认为。那个时候,我们教室都在一栋楼,他们办了《滴水》墙报,展开大讨论:地球化学是不是科学?
开始的时候,许多人认为地化描述性的东西多,缺少定量的数学模型,感觉不大科学。后来讨论的结果是地球太复杂了,从地球几十亿年的演化历史,到地球内部的极高温度和压力环境都很难进行模拟实验,加上它的研究对象太复杂、影响因素又多,所以很难用简单的数学模型描述。地质科学是从描述性的分类科学开始起步的,学起来确实有些枯燥,但这是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不会满足于描述性分类学,我们的目标也是要使地球科学的研究定量化,但需要一个过程。不能说历史上搞地质学、地球化学的人智商低,研究物理的就智商高,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办地球化学专业就是要把学生数理化基础打得扎实一些,以便推动地球化学定量化。我们不应该只是抱怨地球化学不科学,而是努力将“使地球化学走向定量化”当作我们这一代的责任。正因如此,我们要打好地学基础,化学课程和化学系看齐,是甲型的;物理和数学是乙型的,也和化学系学的一样。因此结论是,光抱怨地化不定量是没用的,能不能定量化——责任就落在我们这代人身上。所以可以说那次滴水墙报大讨论得到的结论还是比较正面的。
陈:您入校时是困难时期,当时科大学习风气怎么样?
李:我1960年入学的时候,科大的教学方针就是“重紧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课程要重、抓得要紧、讲得要深。我们开始上普通化学课程的时候,老师一上来就说我们要有微观视角,要站在量子力学角度去理解化学反应,抛弃初中高中学习的一套,第一节课就把我们讲晕了。当时教务长在会上讲科大为什么要搞“重紧深”呢?他说科大培养的人才是搞尖端科学的科学家,就像培养运动员里面的世界冠军一样,那就要搞大运动量训练,世界冠军都是这么练出来的,要攀登科学高峰,就不能按一般的要求。所以当时有说法“穷北大,富清华,不要命的上科大”,就是说我们的课程非常重,讲的又是最前沿,学生玩命用功。开夜车的和开早车的经常在教室碰面。我们那时候从来没有羡慕过北大、清华怎么样,他们是否比科大高一头?我们没有这样的看法。我们只知道我们学风比他们好,我们是要攀登科学高峰的。
后来对于科大毕业生的调研,发现大家普遍喜欢科大毕业生。科大学生有两个特点,第一,基础扎实,数理基础好,没学过的新东西自己摸索就学会了;第二,工作扎实,肯钻肯吃苦,不是夸夸其谈眼高手低的,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都是在大学学习时培养出来的。就连现在,我77岁了,工作起来也还是没有礼拜天寒暑假,都在干活。
我以前在天津上中学时也见过大学生,洋气得很!女生都是穿连衣裙,但是我到北京下了火车一到科大,看到的完全不是这样,穿带补丁衣服的农村孩子非常多,早晨起来大家还种菜浇水,吃饭排队还掏着单词本在背单词。这个大学不讲吃、不讲穿、不讲排场,只讲学习,我当时就感觉自己来到了一个好大学。
我们入学的时候正是困难时期,吃不饱,当时中央提出口号“劳逸结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证身体好,度过困难时期,将来再干。我们同学去八大学院那边找同学玩,回来说:“嗨,人家八大学院都不念书了,该玩的玩,该休息休息。”但是科大没有,哪怕是困难时期。
当然我也不主张开夜车,我讲究效率,坚持晚十点半回宿舍,十一点躺床上。但是那股学习风气还是很好,整个困难时期毫不松懈,没有因为吃不饱就课不上了、作业不做了,没有!我认为科大在当时就养成了这样的学风,并且一直延续下来了,现在虽不像过去一样,但是还是不错的。
二 所系结合,服从分配
陈:您的毕业论文做的是什么?跟着哪里的导师?
李:科大是“所系结合”办学,因为是五年制,大四下学期6月份开始分配毕业论文,当时大部分论文都是地质所老师带,少部分本校老师带。四年级暑假我就去中科院地质所做毕业论文,有两个月,跟老师做高温高压实验,熟悉实验方法,做条件实验。我五年级上学期课程不多,一个是学二外——英语,另一个就是看老师布置给我的50篇俄文文献。五年级下学期我因为去了香山大队搞“四清”,毕业论文就没有做到底。其他同学暑假期间就跟老师到野外采样,制备样品,五年级下学期不上课了,全力以赴做毕业论文,做系统的实验。
虽然就在所里待了两个月,但我还是明白了做科研是怎么一回事情——那就是一定要扎实,从小地方做起,首先要把实验做好,不断总结,改进实验,还要不断读文献,从文献中了解进展,学习他人经验。这是从书本向实际工作过渡的一个阶段。那些做了完整毕业论文的同学可能感触更深,我没做完,我的论文老师很欣赏我,他也觉得可惜。虽然损失了毕业论文,但是参加“四清”工作队了解农村,学习做农村工作,使我的社会工作能力得到锻炼,对中国农村社会有了切身体会,我并不后悔。
陈:本科论文训练对您后来有什么影响?
李:我认为毕业论文对学生最重要的是思维方法训练,而不是说有多高的科研水平。比如我当时做高温高压实验,一做就发现解决实际问题非常不简单。当时我做的是“锡的迁移形式”。锡矿都是热液矿,在一个地方富集成矿,得有一种溶液把锡带到这来,那么锡在高温高压的热液当中,以什么形式存在、迁移,在什么条件下沉淀?我就研究这么个事情。我们的实验就是要制备各种锡的络合物,比如六氟化锡等,在高温高压水溶液条件下观察它是否发生水解,能否保持络合物形态稳定存在。测定方法就是把高压釜淬火冷却后再打开取出溶液测定。这样测定的结果是淬火冷却后的结果,并不代表是高温高压条件下水溶液的情况。如何在高温高压状态下测定高压釜内溶液的络合物状态就成为一个难题。
后来我们想需要设计一种高压釜,将两个电极深入到实验腔内,测量高温高压状态下水溶液的电导率来了解络合物的水解情况。但困难问题是向高压釜内通电极,必须保证电极与不锈钢高压釜和白金实验舱之间要绝缘,还要密封并能经受住高压,不能有溶液泄露。这成为我们面对的难题。
我最后因为搞“四清”没有继续加入,但是后来也没听说他们搞成了。这个事情使我认识到,很多事说说容易,真做起来难题多得很。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其它学科和工程技术的配合,不下功夫不行,仅靠自己力量也不行。所里接触的课题都是前沿课题,是科研一线的真刀真枪,而不是一些拿来练手的练习题。所系结合的好处就在于此[1]。
陈:您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是自己的志愿吗?您当年对于自己的方向、前途有哪些设想?
李:留校不是我的志愿。我第一志愿是到地质队,到生产第一线。当时辅导员问我,我说学了几年最大志愿就是能为国家找矿,给国家找到矿就算学以致用。当时填志愿就是青海、云南、甘肃等边远地带。第二志愿就到研究所,做研究。辅导员问我有没有考虑在学校做教育,我说我没考虑。谈完这话我就琢磨,辅导员是不是想让我留校啊。当时我的成绩是全年级第一,又是校学生会主席,很有可能留校。当时我想留校就留校呗,反正是服从分配。我们当年毕业分配的时候都是这种“螺丝钉”精神。
陈:与您同级的毕业生大多倾向于哪种出路?
李:我们那代人当时都是这种想法:上万上亿的人当中,国家拿钱把我们少数人培养出来了,我们不能和国家讨价还价。有的同学来的时候除了一卷凉席、一个自己做的小木箱,啥也没有。有的南方同学的连褥子都没有,科大校园里冬天很多同学都穿解放军淘汰的棉军服。这些学生都知道,如果不是国家培养,他们上不了大学,所以服从国家需要。那时候我们指导员管分配,说有些同学谈恋爱了,如果照顾你们分到一起,就不能照顾地方了,所以当时分到青海、甘肃的很多同学都是一对一对去的。
当时我们系1958级、1959级同学很多去了中科院或国防科委和国家部委的研究所,也有部分去党政部门,做校长秘书之类的工作。我们那届是1960级,入学80人,毕业70多人,有些人考研到研究所,还有相当一部分去省地质局或者地质队的实验室,在生产一线做工作,就我一人留校,在教研室。
当时同学毕业聊天谈心,有人说:“李曙光甭看你当过学生会主席,你这人不适合搞政治。”我听了不服气,我怎么不适合?不就是为人民服务嘛!从中学起我就是学生干部,做得也不错。那个时候年轻气盛,觉得我干什么都行,也能干好。但是后来经过“文革”,我的想法变了,发现干行政不是我强项,我不太善于做人的工作。我理解到社会的政治工作和学生干部组织活动不一样,学生干部办新年晚会、运动会,都是为大家服务的,不涉及任何利益关系;但是工作之后,发现社会上的事物和矛盾很多涉及到利益分配问题,如何在保证利益分配均衡的同时又能调动大家积极性?其中涉及很多复杂的人的工作,这恰恰是我的弱项。我慢慢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就下决心一直坚持做业务了。
陈:当时有没有考虑过考研呢?
李:我没有。我们那时普遍把考研看得不太重,虽然班上也有一些同学考研究生,不过总的来说大学毕业一般都是先找工作。另外一方面,大四后半学期我被调去搞“四清”,也没有时间准备考研。我那时跟着中央党校高级干部组织的工作队,帮忙做记录、跑跑腿,做青年工作。当时科大调了一批学生骨干去帮高级党校工作队当助手,所以那年冬天我就没有考研。
陈:您1965年毕业,然后很快遭遇“文革”,这对您的工作有何影响?
李:“文革”期间整个教学工作都停了,我毕业以后第一年主要还是下乡搞“四清”。这是我第二次搞“四清”,因为我有之前的半年经验,先在分团干事,然后就是到生产队当“四清”工作队队长。1966年“文革”开始后,我们的“四清”工作结束,我们就回校了。
那时我们参加“文革”,主要就是跟着党中央走,全校都是贴大字报,揭发“资本主义道路”“反动学术权威”。我还被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我是“北京黑市委的修正主义苗子”。起因是因为我当校学生会主席的时候,1963年五四青年节,北京共青团开五四纪念大会,请一些青年作报告,就请了我,说我是学生干部、校学生会主席、学习成绩又这么好,请我谈谈如何处理好社会工作和学习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在学生干部中非常普遍存在,很多学生干部干学生会工作很卖力气,但是耽误了学习。做完报告,北京共青团市委就把会上所有报告结集出版了。此书被学生看见了,他们就帖大字报,说李曙光是北京市委欣赏的人,是“北京黑市委的修正主义苗子”。但这张大字报也没引起后续反应。
“文革”开始后不久,围绕打倒还是保护党委书记刘达,学校师生分成了两派。开始我不参与哪一派组织。1967年中央提出要“促联合”,我认为很对,就开始活跃了。我加入以学生为主的“东方红”组织,后来又被拉到“大联合革命委员会”中。接触以后,我发现两派斗争根本制止不了,因为形成两派的主要原因不在青年学生,而在干部的身上。前后两届党委书记在任用干部方面有差异,这些干部将他们的看法传输给学生,造成的两派的分裂。
“文革”使我理解了什么是政治。有人说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可阶级斗争为的又是什么呢?阶级斗争斗的是阶级之间利益的分配。不同阶层的利益分配,历来是斗争的核心问题。做好政治工作,就必须了解各阶层利益之所在,然后掌握平衡,使社会稳定发展。这需要很高超的本事。我发现我这方面不行,我可能做业务更好一点。所以“文革”后我就坚定当老师,教一门课算一门课,做一个课题算一个课题。有些人说政治是肮脏的,我并不赞同。社会有分工,社会利益分配问题客观存在——总有利益怎么分配的问题,避免不了。我认为:政治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问题在于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这个工作。
陈:科大是什么时候恢复招生的?刚开始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李:1970年科大下迁来合肥。1973年,我们系开始招生。招了生就要上课啊,但是当时从北京搬来的很多东西都是破破烂烂的,“文革”耽误了的业务都要恢复。我负责一个小组建立了一个化学分析实验室,开的第一门课是硅酸盐岩石全分析课;此外我还担负另一门课:岩石矿物鉴定,为这门课我特地去安徽地矿局岩矿鉴定室去实习请教矿物岩石鉴定方法。
这时候数学地质兴起了,我当然很感兴趣——当年上学就一直想要搞地球化学定量化嘛!我们上大学时没学过线性代数,只学了高等数学、概率论,所以我那时有空就去听线性代数课;又因为以前二外就没学过几个单词,“文革”里全忘了,所以开始跟着电台学英语。总的来说,20世纪70年代初是恢复阶段[2]。
三 铁矿会战,初显身手
陈:那么您何时开始独立的科学研究工作?
李:我最早参加的大型科研项目上是铁矿会战,这是1975年国家计委下达的全国性科研任务,科学院全部力量动员起来。当时我是教研室副主任,负责科研,在铁矿会战中加入科学院鞍本队的弓长岭黑富矿组(鞍山—本溪铁矿科研队弓长岭磁铁矿科研组),为解决我国炼钢的富铁矿石短缺的问题,研究弓长岭型磁铁富矿形成条件、找矿规律和成矿预测。我们当时和地化所共同组成弓长岭黑富矿组,我任组长。在这个科研过程中我觉得最成功的是,我把我的数理知识用来找矿。
这个弓长岭富铁矿体呈现东西长条状分布趋势,中央区是主要矿区,西北区少,东南区有断层与中央区相隔,上部勘探结果都是氧化贫矿——那么深部有没有类似中央区的磁铁富矿?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深处有富矿但给不出具体深度;另一种认为断层断距很大,深部也是氧化贫矿。当时我问总工,这个问题你们解决没有,他说没有。我当时正考虑如何利用我数理基础好的优势做些有新意的工作,这个富矿问题正好可以用多元统计做趋势面分析,通过统计模拟中央区西北区矿体走向趋势,向东南区外推,有可能帮助我们做出判断。于是我就对鞍钢勘探公司总工说,如果你们确实认为这个问题有必要解决,我就做,条件是弓长岭矿区所有资料向我开放。他说当然有必要!所有资料都对你们开放。
这个工作的统计工作量相当大。我带了几个学生,把几十年矿区所有勘探和采矿资料综合起来;和数学系合作,用大计算机进行趋势面运算,当时我们就去了上海交大的大计算机上运算。那时候输入数据都是在黑色纸带上搓窟窿办法将数据编码,再将纸带送到光电机上输入。最后根据趋势面结果推测在东南区第25勘探线负500米有富矿体。
当时我们系黎主任(鞍本队副队长)就拿了这个趋势面分析结果去冶金部做年度汇报,根据我们的汇报,冶金部铁矿会战指挥部当即决定调钻千米钻,钻探验证。会战就这个好处,不同部门很好协调,说干就干。那年冬天立马就开始钻探。第二年夏天我再去,就看到当时的孔位打出了13米厚的富矿。我问钻探工程师是根据什么来布置钻孔位置,工程师说就按照你们这张趋势面图做的。当时我感到非常高兴,非常有成就感。深感科大地化对我们的地学加数理化的培养使我们有更多优势,这个任务它需要多元统计,需要计算机计算,还要地质学基础。后来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这个成果还得了奖。
科大培养模式的好处在于,一是强化数理化基础训练让学生迅速学会新东西;第二个就是让人不甘平庸,我们一直有个信念,就是要攀登科学高峰,什么是科学高峰?就是未知领域啊!我们一直在想要用我们的专业优势做点新东西新成果出来。
陈:数学地质带来了看得见的成果,为何您没有继续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呢?
李:对,数学地质很好,但是后来我放弃了,为什么呢?因为全国数学地质大会第二届会议[3]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参会同行感兴趣的是新方法,而不是应用成果。因为数学地质要想做得深,就必须搞方法!而搞一个新的统计方法是专业的数学家的任务,一个回归方法就可能需要一个人搞一辈子,谈何容易!而且我们没有经过数学专业的严格训练,搞不了这个。后来我就感到,数学地质作为应用手段拿来用可以,但是我们这个科学背景的人没法攀登数学地质高峰。所以我还是搞我的地球化学。
四 公派麻省,“三严”精神
陈:1983—1986年间,您被公派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球与行星科学系进修。当时主要做的研究是什么?
李:我在美国做课题,教授不干涉,大部分样品是我从中国带去的,他只教我方法和态度,我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跟他们学了锶钕铅同位素分析确定技术,参加讨论,开阔视野。在麻省理工进修给我影响最大就是他们严肃的科研态度和严格的科研作风。我当时主要做两个研究,一个是继续铁矿会战时期做的太古代同位素年代学研究;另一个是研究秦岭、大别山采的样品,做造山带的年代学和地球化学研究。大别山榴辉岩的年龄研究就是其一。我在国内铁矿会战时期是做找矿应用,出国更多做基础研究,这是研究方向的大变化。
陈:当时您对中美科研环境有哪些体会?两者差异是在科研硬件方面,还是在制度政策等软环境方面?
李:当时两国科研硬件差异客观存在,这个不必多说;软环境差异主要表现在科研传统,比如他们更关注有全球普遍意义的基础科学问题;他们做基础研究有严肃、严格、严密(“三严”)的作风和传统。拿我们地球化学样品的制备来说,铁矿会战时候我们是和矿山碎样车间师傅学的,把岩石,矿石往“老虎口”碎样机一送,“哐当哐当”倒出来就是样品小碎块;用鼓风机对着碎样机呼呼一吹,这就认为机器吹干净了,第二个样品就又倒进去了。“老虎口”出来的小碎块,也不挑选就进入对辊机,捻成米粒大小,然后装入棒磨机,出来就是粉面,流水作业,非常快速。每换一个样品,对机器不是用鼓风机吹一吹。就是拿个抹布把棒磨机样品罐子擦一遍就算干净了。
我们以为这样加工样品就可以了,但是到了美国以后我们才发现,人家加工样品完全不是这样。一个岩石样品拿来,人家先用切片机切成薄片,用砂纸在水中打磨掉切面的锯痕,再拿白布缠上,放在木头墩子上,用灌了铅的塑料锤砸;砸成碎块再挑,有气孔的、风化蚀变的都不要。然后用纯净水超声波洗,干净了放在烘箱烘干。挑纯洗净的小碎块放在碳化钨的震动盒震碎成粉末。每换一个样品,震动盒都要水洗干净,然后用纯净水淋洗一遍,最后用分析纯的丙酮淋洗,驱赶水膜,挥发干了,再上第二个样。这样的样品加工程序使得样品没有外来污染,也没有样品交叉污染。我在矿山上一天流水作业几百个样,在美国光做震动盒这个步骤一天就6个样,一个礼拜40个样,保证没有污染。
我感到这才是做科学实验,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国内学的那个做法是工业生产流程,铁矿石铁含量是35%还是37%在生产上没有大的影响,但是基础科研这个精确度不行。这种科研的态度,对我后来做大别山的工作影响很大,它使我做的年龄的准确度经得起检验。
大别山榴辉岩是华北和华南两大陆块碰撞的产物,准确测定它的形成时代可指示这两大陆块的碰撞时代,因此成为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热点。但不同研究者测定的年龄值差异很大。有一次全国同位素年代学会议的大别山同位素年代专门讨论会上,我问一位报告不同年龄数据的年轻研究员,选矿师傅挑好的样品你还做不做进一步挑选?他说那还挑什么呀,选矿师傅给的矿物纯度达到99%!我说那还有1%的误差呢!你知道我们同位素分析精度多少吗?那是百万分之几。即使矿物纯度达100%,也还要进一步精挑,除去蚀变颗粒。他说那没多大影响。我说我做过,影响大了!——这就是观念不同,大家都认同要严格,但是什么才叫严格,大家的标准却不相同。
陈:出国学习对您而言,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李:第一,就是刚刚说的体会到什么叫科学的“三严”精神:态度严肃,方法严格,推理严密。第二个国外收获就是开拓视野,关心什么样的问题,国内很多都是关注局部的区域地质问题,对于学科的基础科学问题研究不够。第三个就是英语,上大学我只学了半年二外,后来跟着电台自学,访学期间听、说、写都有提高,后来一些国际学术交往我也就靠着那两年底子。
这三项收获对我后来影响匪浅,为什么我的大别山定年工作是精准的、经得起国际同行和后来新方法的检验?这没什么窍门,就是保持“三严”工作态度和作风。那时国内同行挑样品没那么严格,有的研究生怕挑样品、懒得挑样品,他们嫌费劲,那怎么能行?不管费多大劲都得严格地挑!不然都白做!
五 科研传统,代代积累
陈:结束两年多的进修归国之后,您又开展了哪些研究?
李:前面说过,在国外我研究了两个内容,我回来以后这两个方向其实都能做。太古代研究,国内有几个做得好的单位,地科院有程裕琪和沈其韩院士;中科院地质所赵宗傅先生带了一批学生,力量也很强,我要做这个领域无竞争优势不上去。但是大别山榴辉岩定年我是第一个,占了先机。正好我1986年回来以后,地质所李继亮研究员带着瑞士许靖华,土耳其辛格、和美国罗杰斯教授这些海外科学家一起到大别山去跑野外,我也参与其中。许靖华对我的大别山榴辉岩定年结果是三叠纪很感兴趣,他说他们对阿尔卑斯的研究就是依据的榴辉岩定年,你这个大别山定年结果和我的观点很一致。这使我感到大别山榴辉岩定年工作是很受构造学家重视的,解决华北和华南陆块碰撞时代是意义重大的选题。于是我的第一项基金申请就是申请“华北和华南陆块碰撞时代的釤钕同位素年代学研究”,这是我从美国回来后做的第一个研究。
陈:回国后您感到中国的科研环境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李:回国之后,我感到国家科研环境最大的变化就是成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方便青年科学家申请科研资金,尤其对起步的年轻人是极大的解放,学校也鼓励你申请,这笔钱也由你对基金委负责。基金委项目申请什么课题没人干涉。所以有人说科研不自由,我说有什么不自由?没人干涉你的科研选题,关键是你申请研究的课题的意义和可行性要得到同行认可。我回国以后全部科研项目都来源于基金委,我也没有实验室,野外、大山就是我的实验室,我的样品都是我亲自在我地科院老同学那里做的,或者出国做的。
陈:三十多年过去,现在中、美两国在科研方面差异又如何?您如何看待关于“中国在科技、经济方面已全面超过美国”的说法?
李:现在我们的论文发表在国际上排第二,大量论文能够达到国际认可标准,早些年不行。现在中美两国的科研差距可以说是缩小了,个别领域已经追上,甚至稍稍领先,比如量子通讯科学。但是全面地来看,这个差距还很巨大,需要继续努力。比如科研传统,它就需要一代代积累,它体现在个人身上,因此个人的“三严”精神很重要。我曾经与侯建国交流,觉得我们这一代科研人,都是过渡性的,起着传帮带的作用,最后攀上科学高峰的是后代,比如潘建伟这代人。
陈:您认为高校的科研,与中科院、部委研究机构、地方研究机构、军口研究机构的科研有何区别?
李:高校科研做的更多是自由探索,占国家经费小头;但是研究所、部门研究院往往有国家目标国家任务,比如铁矿会战目标就是要找富铁矿,这些研究必不可少,这些研究是我国经费大头,美国也是如此,比如NASA就是目标明确搞星际航行。
这两种呢,国家都需要,特定时期国家急需任务可能更重要,但是要有适当平衡,一定要保证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要不然就没有未来的新领域发展。比如量子信息,很多人开始还不接受,现在要建立国家实验室,目标就很明确了。但是量子信息也是从自由探索发展起来的,所以自由探索必须要有。另一方面,国家集中力量也必须有,不然都自由探索,做一些小玩意,国家发展需要的东西怎么办。航母是大目标,其他水下的武器也是有必要探索的,不然老是那个东西。国家目标占大头绝对没问题,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如此,问题是自由探索不能消融,它已经只是个小头了。
另外从培养人才角度来看,基础研究更有利于培养博士生。自由探索题目专尖,博士生在基础问题上钻进去,可以在短短四、五年时间里获得完整训练。研究一个问题从文献调研、实验、理论分析,最后写作成文,他可以得到全面地训练。但是要造一个大桥之类的实际项目,它需要分工,就算是博士生,一个人也不能从桥的整体设计、力学结构,一直到最后的材料都参与解决。工程方面的人才培养和成长我没有经验,我想离不开通过重大工程项目的实践和长期积累,可能与基础研究训练有共性,但不太一样。
陈:那您认为研究生博士生的研究成果的价值通过什么展现?
李:学生的研究成果的价值,基础研究方面就看创新性,应用型题目尤其是信息技术类就看应用效果如何。我认为对于一个学生的训练,更重要的是作风和方法的训练,他们不一定毕业后一辈子就干这个,但方法和作风是受益无穷的。
陈:您认为师生关系应当是什么样的状态?
李:硕士生、博士生和老师是战友关系。老师是指挥员,研究生是班长、战士,同一个目标都是攻上山头,共同完成课题。老师的作用在于选择方向,这个方向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要根据很多调研,要做预研究探索,要找到突破口,要总结失败经验,他还要去找钱;好的师生关系应该是这样:老师因为学生优秀,培养了优秀人才而高兴;学生因为老师指导少走弯路,为自己今后发展打了底子而感激。这是一个共赢的关系,而不是谁在为谁服务。
[1] “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是中科院1958年创办科大时就确立并一直坚持的办学方针。整合学校院系与各研究所之间的优质教育资源,沟通学术研究和市场产品,既拓展了学生能力的边界,也拓展了科研价值的边界。
[2]1969年,由于多种原因,原址位于北京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于湖北、河南、江西、安徽多地寻找学校的疏散地址,最后定于安徽合肥,并于1970年10月基本完成了下迁(现在也叫南迁)。当时条件艰苦,教研工作难以全面开展,直到1973年才恢复招生。在恢复期间,学校的仪器设备图书档案均损失惨重,教授讲师也大量流失。
[3]第二届全国数学地质学术讨论会于1981年4月21日至25日在长沙召开。会议是由中国地质学会数学地质专业委员会筹备组和湖南省地质学会主持召开的。出席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代表来自地质、冶金、石油、建材高等院校,以及中国科学院、国家地震局的专家、教授、科技人员共300多人。
致谢 本访谈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熊卫民教授在“口述历史理论与实践”课上出题,访谈时得到了张雲涵同学的帮助。
陈雪纯[收稿日期:2018-09-10]
作者简介:陈雪纯,1995年生,安徽合肥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与科技政策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影视符号学,辅修口述历史。Email:
(本文首发于《科学文化评论》2018(6):94-106.)
2019-06-26 上一篇: MIT科学家实现电子束操纵单原子 下一篇: 七中国科大人晋IEEE会士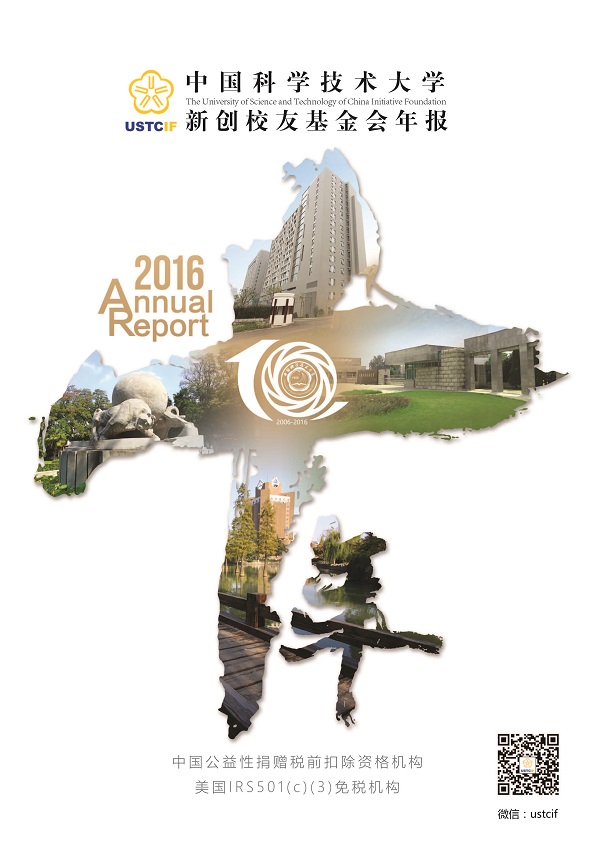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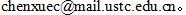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5836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5836号